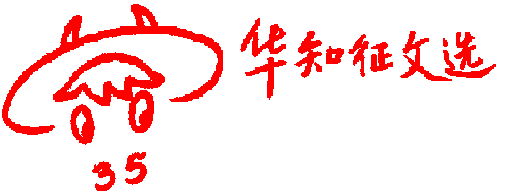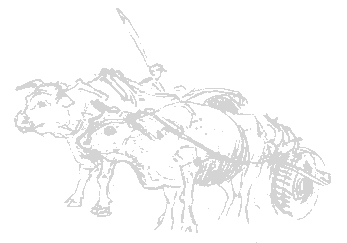| 抗 拒 下 乡 |
|---|
老 杏 |
|
上山下乡是一段历史,抗拒下乡也是这段历史中的小插曲。 我没有下过乡,一方面是自己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偶然的机遇。也许是我的初中班主任不热衷于动员上山下乡,我们班竟有十多个同学留在了城市,其中不乏毫无背景的家庭。以至于后来看到关于下乡动员的严厉无情时,认为长沙可能不像其他城市搞得那么紧张。 从小对大自然的奥秘有浓厚的兴趣,也怀有深深的敬畏。读小学开始爱上了无线电以及模型制作,读中学后又迷上照片洗印,摄影当时还没条件,可望而不可及。读中学时每期都要支农,每次都是走路下乡,途中要经过当时的无线电工业学校,那是个部级中专。我心里暗暗给自己定位,初中毕业来报考这儿,也可以圆自己已经作了几年的梦。实际上那也是一种天真幼稚,当时无线电属于特种行业,对“家庭出身”要求更严,如果没有文革有幸参加中考,即使是中专大概也会与我无缘。从初二开始“贯彻阶级路线”,对我们这些不良家庭的子弟是一闷棍,读书深造成为了泡影。 进入初三学校就开始对毕业生进行上山下乡教育,一次政治考试的一道大题是谈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试卷上不加掩饰地说不愿意下乡,理由就是我的爱好和志向适合在城市发展。尽管在最后勉强加上“如果是祖国的需要,我还是会高兴的去……”,老师阅卷时毫不留情只给了50分,得了中学考试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这次考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就是不去”的逆反心理产生的根源之一。 文革中还有一件对我人生之路影响很大的事,那就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回城造反。我的表哥表姐和从小到大的伙伴中也有老知青,那两年都回到了长沙。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到了一些知青与当地人的冲突,了解到农村落后愚昧的一面。当文革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政权的权威被打翻在地,这些累积的冲突演变成一桩桩血案。由于那一次不及格的考试还记忆犹新,我对这方面的见闻特别感兴趣。当时长沙的知青文艺宣传队“红一线”也很有影响,他们的演艺算得上数一数二,而且那些节目极具煽动性。实际上那些节目的实质是对所谓的贯彻阶级路线的控诉,制造新的血统论,人为地把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划为三六九等,是当时的执政者作出的最愚蠢的决策之一,把一大批有为的年轻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一九六八年的“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并没有上课,接到通知回学校,紧接着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刚开始传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就有不少老三届学生响应号召,我二姐也自愿报名,第一批下乡去了沅江黄茅洲。 我当时已经对上山下乡产生抵触情绪,虽然嘴里不敢明说,但就是不报名,推说先看看去什么地方,于是又开始了一次新的“串联”。首先我去了汨罗,这个县是建国后新划分的政区,以流过县区的屈原投江的汨罗江命名,一位儿时伙伴正好下到我家有个亲戚的公社。我先在亲戚家住了几天,带了一台自制的半导体,到了晚上亲戚家挤满了人来听收音机。差不多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来听过,很多人是第一次听收音机,小孩子的问话最有意思:盒子里唱戏的人有好大?去知青点后在那儿度过元旦,印象最深的是元旦前夕,开始是买了点心、白酒以示庆祝,大家干杯祝愿,朗诵豪言壮语的诗句,最后由点上唯一的女生——一位高三男生的朋友——带头,演变为相对而泣。在那儿的几天和朋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话说大部分的时间大家都还是很愉快的,劳动强度也不大,只是晚上的时间难得打发,常常是嬉笑打闹突然变为冷寂忧郁。 从汨罗回长沙后在家里呆了些天,二姐托信说给我在她们大队的另一个生产队开了一张接收证,希望我和她下到一起互相有个照顾,于是我又开始另一次考察。去汨罗是坐火车,沅江在洞庭湖,这一次是坐轮船,一起乘船的还有一男一女,也是二姐同学的弟妹,他们两人都比我稍微小一点,已经转了户口带着行李前往乡下报到。那女孩子显得特别柔弱,她家里只有母亲,父亲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路上总是心事重重,只有在我们有意逗她开心时才腼腆笑笑。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二姐当时开的接收证托人带回长沙,也就是一张盖了生产队公章的信纸。当时湖区的生活相对来说比山区稍微好一点,她的一个同学把这张接收证扣住想留给自己,好在我并不怎么在意,要了两次不给也就算了,但是对那位大姐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我们的船不是直达,中途还要在一个叫茅草街的地方转船,到达茅草街已经是晚上,转船的百十来个知青就在码头过夜。湖区的气温比长沙低得多,冬夜寒气逼人,不多久人就冻得受不住了,这些省城来的年轻人开始四处搜寻可以取暖的物件,码头上到处燃起一堆堆柴火。第二天早上,码头的竹栅栏都不见了,连厕所的隔板都烧掉了几块,我估计那些凳子椅子恐怕也烧掉了一些。 到达二姐的生产队,见到了他们知青点的十个姐弟,他们点有个特点,男孩的年龄全部都比女孩小。女的都是高中生,男的都是初中,其中三对姐弟,另外两个男孩也是堂兄弟。那位堂兄一表人材,虽然年龄不大却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从江永转点到了这儿。后来我了解到他原来是一中的初中生,父亲是旧军官,自己由于一个什么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案初中没毕业就被迫下放江永。堂弟叫志远,性格谦和,那些天我和他一起的时间最多,回长沙后在家休养的一段日子我们来往很多,一度成为好友。 在沅江的日子里有一件新奇事,我帮他们一起给知青点的房子涂牛粪。那儿的房子都是芦苇秆编织成墙板,然后糊上一层泥,表面再糊一层牛粪,那牛粪的作用类似于纸浆增加泥墙的结构。这种房子的特点主要是造价低,还有就是不怕水淹,淹过后重新抹一层泥又能住。我到那儿房子刚砌好不久,参加了最后的这道工序,满满一桶搅匀的牛粪浆,用手抓起来一把一把糊到墙上尽量把它抹匀。可能是天气太冷分子运动不很活跃,不觉得很臭,却有一股青草的气息。没抹牛粪之前泥浆上裂开一道道缝,我领教了湖区的寒冷,早上起来,夜晚呼吸的湿气在被子上凝成了一块冰,对于刚到湖区的我来说,既新奇又觉得不可思议,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竟然也能度过冬天。 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前,去乡下转了一圈的我传染了急性肝炎,志远也与我同时患病,在家休养三个月后才基本痊愈。当时我家所在的宿舍被划入扩建的一个纪念馆范围,大动员时由于纪念馆拆迁搬到了相隔较远的一个大院,父母被那些无休止的运动整得晕头晕脑,没有及时迁户口,无意中躲过了居委会动员这一关。我推测当时的居委会成员可能也是不得已进行下乡动员,有谁愿意自己的子女远走他乡?人搬走了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新搬的地方没有户口自然没有责任,也不清楚情况,于是我这儿变成了无人问津。我想大概是无意中逃过一劫,以我对父母性格的了解,他们还不会想到有意采用这一招。 随着身体的痊愈,精神上的折磨日益加重。走出家门,到处都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户口已经迁过来了,免不了也要听一些人的闲言闲语。多亏落难之时有贵人相助,二姐的一位同学在区四个面向办工作,她说按政策我的情况可以病留,给我办了一个留城证,取得了类似于现在暂住证的一个合法身份。虽然人是留下来了,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在还有那一大堆无线电零件可以打发时间,没事就翻来覆去地装拆收音机。一个人在家没事找事,带上耳机收听境外广播,台湾的当时控制很严,一般都有很大的干扰声,但美国之音、莫斯科电台、香港的福音都能很清晰的收听到。 当时最兴奋的时候是乡下的同学回来之时,中学小学的同学只要回家都喜欢到我家来,总有一些事情要我帮忙。修收音机是不用说的,还有什么洗照片呀,做些什么小玩意儿等等。小提琴的肩垫做了好些个,以至于一位同学的女农友好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我是木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得意之作,给一位同学做了一盏直流的日光台灯,灯罩部分又可以卸下来装在他的谱架上,可惜他还没带下乡去使用就不知被什么人顺手牵羊给偷走了,也可见那个制作的确逗人喜欢。那些日子里,我的知青朋友比下乡的更广泛,就像滚雪球,一个点上有一位朋友就结识一群,远远超出了同班同学的范围。在我这儿朋友们能满足不同的爱好,喜欢音乐的为收音机而来;喜欢照相的来冲印放大,我有显影罐和自制的土放大机;还有喜欢下围棋和喜欢聊天的,当时那些朋友们给我的评价是“什么都会玩”。 中学读的是男子中学,小学的女同学基本上已没什么联系,我的朋友中异性凤毛麟角,y是其中的一位。从小就在一起,像兄妹还是青梅竹马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更像哥们儿。她是那种理想化的姑娘,没去富裕的湖区而下到了边远的湘西山区,寻求山林召唤那种浪漫的色彩。第一次回家探亲,来我家描述她们的知青点,大山的巍峨,知青们原始公社般的生活,讲得眉飞色舞。也许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她的到来一度动摇了我抗拒下乡的决心,竟试探地询问我是否能去她们生产队落户,引得她连声叫好,大概是认为征服了一座落后的堡垒。谈到了她们那儿收音机的信号微弱,我给她出主意解决,回去后架一根户外天线,器材包在我身上了。答应了就立刻行动,当天就在院子里架起绕线机用废漆包线绞了一根十多米长的多股天线。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虽然自己动摇了留城的信念,开始憧憬遐想农村生活的浪漫,最终我还是铁下心来放弃了任何下乡的想法。几个月后,y从海南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想起该给家乡的朋友写封信了,还是那样的理想化,南国的风光、橡胶园的工作、兵团的建制等等,最后还不忘写上欢迎我到海南来,但这一次我已经恢复了平日的冷静。y去海南可能也是家里的意思,几个哥哥都去了那儿,兄妹之间互相有个照顾。虽然我们的交往还不过是朦朦胧胧,但我能感觉到她家里对我们的交往很敏感,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年轻的我在别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少年老成的印象,也包括她的父母,经常要她的小哥——我的哥们儿——向我学习。只不过他们的双重标准有点伤人,可以当儿子的好朋友甚至榜样,要做女儿的朋友那可不行。不过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可以理解老人们的心思,都是那样的家庭,不说攀龙附凤,总希望子女能找一个腰板硬一点的人家。那个可悲的年代,造成了多少悲欢离合,也强扭了多少苦瓜留下多少苦果,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往日的苦涩也渐渐淡化。 接踵而来的是又一次打击,在外地工作的老兄被打成现反入狱,我想找一个正式工作的希望成为泡影,从此开始了我的流浪打工。这一打流就是十年,除了赚钱吃饭看不到任何前途,那样的日子可以把意志不坚强的人逼疯。流浪打工也还是产生了副产品,为了生存而掌握各种技术,为了麻醉自己而把自己的玩家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十年的临时工生活酸甜苦辣,最终还是因为有专业技术,而且五花八门样样都会被现在的单位接纳,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个条件,那时候老兄已经平反。恢复高考时朋友们劝我参加复习,口头上我说快三十的人了不愿意让家里供养读书,实际上心里明白根本不可能通过政审那一关。 写出当年的这些荒谬事实,让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看一看,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辈经历过的苦难,共同谴责、唾弃当年那些人为的愚蠢创举。
(2003-07-20 于长沙) (责任编辑:冒冒) |
| 投稿 评论 上一页 下一页 回顶端 |
| 华 夏 知 青 网 版 权 所 有,未 经 作 者 允 许 禁 止 转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