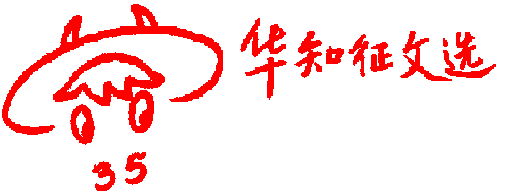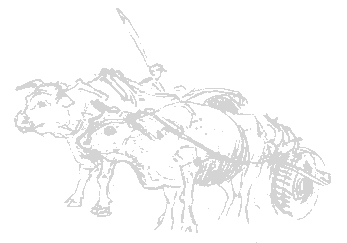| 半 个 江 梅 |
|---|
乃 枫 |
| (长篇小说节选) |
|
三 葱屯生产队派来接知青的,是个机灵的小老头。老头说,他姓钱,是生产队的贫协主席。这个钱老大爷虽然没有吹糖人的山西老头那么老,却已经弯腰驼背了。他空身穿着件开花的破棉袄,腰里松松垮垮地系了半条细麻绳。他把棉袄的领口子使劲敞开着,露出他黑悠悠的满是肋条骨的胸膛。 跟钱大爷来接他们的,是一头拉着崭新胶轮大车的老母牛。老母牛头上戴着一朵纸扎的大红花,看上去,比那个赶车的钱老大爷可神气多了。虽然它又黄又瘦,走路磕磕绊绊,可它拉着的那辆胶轮车却是嘎嘎新的,显得与牛不大相称。胶轮车上,用高粱秆编成的草帘子密密麻麻围起来,围成一个大“车箱”。“车箱”上贴了一圈红标语,左边一条写着“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右边一条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赶车的钱大爷说,那头老牛可是头典型的“革命的老黄牛”,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它都一直跟着他,是他的老搭当。年轻的时候,那头牛可是了不得,一个“人”就拉得动一车柴。如今它“人”老了,没有了早年的那把子力气。平常干活的时候,他总是设法照顾它。他还在车辕上加了一条皮带子,拉不动的时候,他就插进一只膀子帮它拉。今天接人的活儿,是他特意跟队长要求来的,还特意给他的宝贝牛换了台胶轮车。他说,胶轮车拉起来比木轮车“轻省”。再说,迎接知识青年进村,大小也是村里的一件喜庆事儿,拉辆木轮车,有多么不体面。 “工宣队”的队长李万昌,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戴一顶没有帽徽的黄军帽,看上去最多不过四十几岁年纪。虽说他是个老牌复员兵,也是城里来的,可他是个“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出身。乡下的事,他全懂。此刻,听得“贫下中农”老大爷关于爱牛的一番话,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立即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就地开了一个即兴的“现场阶级教育会”。他手里挥动着包了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本,一字一顿地做起了报告: “知识青年同志们啊,你们听听,刚才贫下中农钱老大爷爱牛如爱子的一番话,说得何等地好哇!它说明了,广大贫下中农,对牲口,对牛,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十个孩子都是十六七岁。虽说是第一次看见牛,却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一头牛感动不已,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只管让李队长说得满嘴里冒唾沫星子。 “人跟牲口有什么无产阶级感情?”江梅贴着祥子的耳朵,轻轻把嘴一撇。 “别打岔,听人家往下说嘛。”其实,祥子自己心里也正胡涂着。 “可是,你们知道广大贫下中农,为什么会对牲口有如此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吗?”李万昌继续着。 “不——知——道——”孩子们异口同声。这么深奥的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就是因为,牲口是人民公社的财产,广大贫下中农爱牲口,就是爱人民公社﹗爱人民公社,就是爱共产党!换句话说,广大贫下中农,爱牲口,就是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里一激动,手里的语录本掉到了地上。“爱牲口,就是爱社会主义﹗” 他跨前一大步,将《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拾起来,歉意地放近嘴边用热气“哈”一“哈”,再撩起衣襟擦一擦,继续着他的演讲。 “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多伟大呀!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是他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你们想一想,要不是今天你们上山下乡,来到这里,你们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广大贫下中农是如何爱牲口的吗?” “不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才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哇﹗多危险哪!” 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李队长说的危险是什么,站在后面的几个交头接耳起来。 “后面的,不要开小会。”他用语录本指指交头接耳的几个,把危险说得清清楚楚。“你们的思想,跟贫下中农有多大的距离呀?﹗你们再想想看,如果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你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们待在城里,不经风雨,也不见世面,不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脱几层皮,擎等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还不出修正主义?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呢﹗同志们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哇!从修正主义的死亡边缘上,把你们给挽救回来了呀﹗……” 李队长情绪激昂地把报纸上背下来的话说一遍,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他的女儿也是同一批下乡“秋原”,这会儿他正揣摩着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该到了。 孩子们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李队长把女儿的心思放在一边,带头喊起了口号: “向贫下中农学习﹗” “向贫下中农学习﹗”孩子们连忙跟着喊。 “向贫下中农致敬﹗”李队长把《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过头顶。 “向贫下中农致敬﹗”孩子们也把《毛主席语录》举起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口号喊完了,紧接着七手八脚装行李。老钱头瞅个空子把李队长拉到一边,悄悄在他耳边说了半天。李队长极不情愿地点点头,看看行李装得了,他清清嗓子,公布了一项新决定: “我代表第一百一十六中学党支部,作出临时决定,为了表示我们向广大贫下中农学习的坚强决心,今天的牛车我们不坐了﹗我们今天要……”他迅速地组织了一下词句。“那叫……步行三十里崎岖路,扎根葱屯干革命!” 两天了,十个孩子下了火车换汽车,整整坐了两整天,屁股都坐麻了,此刻,他们正恨不得下来走走。再者说,出门都两天了,只觉得山越走越多,路越走越窄,什么都还没有看见呢。至于那大山的背后,那窄路的尽头究竟还藏着些什么奥秘,此刻也正想一头扑过去看看。李队长说要步行,步行就步行,正合孩子们的心意。 赶牛车的贫协钱大爷可高兴坏了。别的不用说,先说他的宝贝牛“轻省”了。高兴之余,他还真的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个叫李万昌的队长。他心里说,“我刚才叫他帮帮忙,无非是叫他跟孩子们说说,看能不能可怜可怜牲口。到底是城里人,真会说话。你看看,一样的事儿,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一说就是一个理儿。这事儿,简直叫他给生生地说活了。”见孩子们也都是满口答应,越发乐得老头儿合不拢嘴。 “年轻人腿快,三十里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钱大爷打了个响鞭儿,“我年轻的时候,三十里路,一头晌能打一个来回。” 开现场会耽误了功夫。等把一切都折腾完了,再等装了车,到上路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三点多钟了。十月辽北的天气,活像个三岁孩子的脸,三笑三哭的,说变就变。钱大爷刚才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如今,话音还未落,它就呼啦一下变了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一股脑倒下来,来不及问发生了什么事,浑身上下就已经湿得透透的了。牛车上的行李都是用被褥卷成的卷,怕人的枕头、衣服和零星物全都塞在里边。如今,叫雨水这么一泡,一个个凭空胀大了差不多一倍。绳子一绷断,行李就开了花,“肠子、肚子”淌出来,零零落落地撒了一路。 男生的,问题还不大,反正没有什么怕人的东西,破了就破了,撒了就撒了,抓起来,随便往哪里一塞就是。女生的,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各色各样的小衣物,花花绿绿地掉进了路边的烂泥里,拣与不拣都不是。不拣吧,日后用了怎么办?要想拣,又实在不愿意当着男同学和陌生人的面,承认那些稀罕物是自己的东西。 江梅的行李卷个头最大,自然破得也最早。眼看着掉进烂泥里,花花绿绿地撒了一大堆,江梅看着,急得差点哭出来。祥子见状,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茄克衫,一把将那堆东西全盖住,不由分说,连泥带水地抱起来,重新塞到车上的一个角落里。江梅看着她的祥子哥,又是感激,又是羞。 好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刚才祥子抓得急,不料漏掉了一件粉红色的小东西,江梅认得,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件小胸衣。这时候,牛车已经走出了好几步,回去现拿,显然来不及,叫别人看见,那有多叫人难为情?江梅无可奈何地看看祥子,心里直叫可惜,祥子也歉意地冲江梅吐个舌头,他也是束手无策。恰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孙志的男孩子跑过去,用两只手指把那个小东西捏起来,大大方方地跑到江梅跟前,就那么直统统地一下子递到江梅手里。江梅接过小胸衣,羞得使劲低着头,老半天也不敢抬起来看人。 孙志和江梅是一个班,又是江梅的同桌。从江梅上中学的第一天起,祥子就注意上他了。他虽然个头比祥子高不少,人却长得精瘦,很不起眼的一副样子。可是,就凭他这副样子,全校上下,竟然数他是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红人”。人家出名,祥子不吃醋,再说人家出名也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阵子,人人都想有个毛主席像章。搞得到的,沾沾自喜,四处炫耀,搞不到的,抓耳挠腮,挖门盗洞。后来,孙志不知在哪里搞到了一枚,本来心里很高兴,可是戴出去跟人家的一比,才觉得他那枚逊色多了。他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就想出一个出人头地的好主意——他把毛主席的像章真的给别在“胸前”了。人家说的“别在胸前”是指别在胸前的衣服上,他不是,他把那像章直接别到了胸前的肉里。这事怎么说?杀了头,祥子也没有人家那份勇气,叫他佩服。那天,孙志光着个膀子,到“停课闹革命”的学校里逛了一圈,临了,还特意在街上兜了个大弯子,就为叫他们好好开开眼。可了不得,不光是在学校里成了“大红人”,全市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抓了他“革命小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先进典型。当然,后来他的伤口感染、化脓,得了败血症,又是住医院、又是打吊瓶,那是后话。到如今,胸前还留这一个大疤痕。 说实话,祥子不是对毛主席不忠,也不是不想出人头地。这事怎么说?既然他自己没有人家那份勇气,就得佩服人家。可是,不知为什么,祥子就是打心眼儿里讨厌他,甚至有些怕他。他刚才跑到江梅跟前献的那份殷勤,叫江梅当着众人跟前丢了面子不说,更叫祥子吐不出、咽不下的。祥子心里的气绝不打一处来,甚至想叫住他问问。祥子除了气,还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他认定,他往江梅手里递那个小东西的时候,好像还特意碰了江梅的手一下。刚才,他自己用茄克衫包了江梅那么一大堆东西,总共才用了不到十秒钟,他的动作甚至神速得叫别人无法察觉。可是,如今这小子,就拣那么一丁点小东西,却如此兴师动众,还故意磨磨蹭蹭,叫众人把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明摆了叫人难堪吗?谁用他来拣了?江梅明明已经放弃不要了的。再说,就是拣,也用不着他那么个拣法,还亲自递到江梅手里?递给他祥子,待会儿趁人不注意,悄悄塞给江梅不就得了?“你小子当了个大英雄,可叫江梅难堪死了。”祥子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盘算着,这事儿,不能算完,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他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觉得别扭得很。 泡散了花的行李继续在水里泡着,依然越泡越大,眼看着就要撑破封车的绳子。高粱秆帘子上的大红欢迎标语,此刻早就冲得无影无踪。十个孩子,围着行李车,脚底下迈着小碎步,双手捂着挨在边上开了花的行李,哭都找不着调了。至于那个“到大山的后面,到窄路的尽头看看”的兴趣,此刻早就荡然无存。 那头老母牛更是惨不忍睹。它拉着越来越重的载,一路上,像个探路的瞎子,每走一步,都得把蹄子抬得高高的,小心翼翼地试探三两回,才敢真的迈出去。看了它那个一步三摇晃的样子,真叫人于心不忍。再看它头顶上,那束纸扎的大红花,早就淋成了红纸浆,沿着脑门流下来,血淋淋地染红了半个脑袋,像刚从屠宰场跑出来的一样。平日里不下雨,这三十里山路叫它一气走下来,怕也够它受的。如今,天上下着这么大的雨,拉着如此重的载,路又滑得像抹了油,就算孩子们是跟着走,那也帮不了它什么忙。看样子,叫它一步一寸地挪到如今,已经不易了,再往前走,说不定真会要了它的老命。眼看着过了前面那个山包葱屯就到了,它却“咕咚”一声连车带牛掉进坑里——坞了车。李队长见状,奋不顾身地脱下自己的黄军装,三把两把卷起来垫到车轮底下,车轮却纹丝不动。他突然意识到,牛车不是汽车,牛不拉,轮子垫起来也不会动,他这才想起去搬车轮子,搬了几搬没搬动,他急了眼。 “知识青年同志们,前面就是葱——屯——”他像样板戏里的郭建光一样,抹一把脸上的雨水,顺手向前一指,“党和毛主席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这是你们迈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步﹗来,女同学都到后面推,男同学,那边三个,过我这边来两个,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搬车轮子﹗”他对赶车的钱大爷吩咐道,“钱大爷,你到前面去赶牲口﹗”他指手画脚地作出了果断的决定,完全像个久经沙场的大将军。他越说越急眼,干脆把身上惟一的一件球衣也脱下来,狠狠地往泥潭里一摔,“肏﹗”他信口骂了一句,赤膊上了阵。 孩子们见状,惊得目瞪口呆。孙志第一个冲上去,领一个过去搬那边,祥子和留下的另外两个搬这边,五个姑娘们也呼啦一下子冲到了牛车后边。 “好了没有?”李万昌队长光着膀子,用一个肩膀抵住车轮,双手狠狠扣进车轮的空洞里。他屏住呼吸,大声喝问。 “好——了﹗”十个孩子们外加轮着鞭子的钱大爷,众人异口同声,严阵以待。 “一——二——三﹗” “嘿﹗” “呃,呃﹗” 牛和车都纹丝不动。 “再来一遍一、二、三﹗” “嘿……﹗” “呃……呃……﹗” 牛和车依然纹丝不动。 车老板老钱头这个时候也顾不得爱惜他的宝贝牛了,他举着鞭子,“呜哩哇啦”地一顿乱抽。起先,那老牛还比比划划地假装拉两下。到后来,它干脆往泥水里大大方方地一躺,心里话,“任你怎么打吧,今天,老子我就是不动了!” 城里来的十个孩子,哪个也没走过路,尤其没有走过山路,更没有谁在这么大的雨里走过。连冷带累,小腿已经开始抽筋。整整四个钟头淋在雨水里,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有一条布丝是干的。脚上的“解放鞋”早就走烂了,“呱唧”,“呱唧”地淌在泥水里,已经踩成了两个烂泥坨。两个泥坨子越踩越大,两条腿就有千斤重,踩下去便拔不起来,使劲一拔,脚出来了,鞋却还留在烂泥里。孩子们,有一半人的鞋子早就不知了去向,他们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跌倒,一身单衣服,从里到外全都糊满了泥浆。糊满了泥浆的单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叫北风一吹,冷气就一直钻进心窝里。酱紫色的嘴唇一个劲地打着哆嗦,上牙碰着下齿,迅速地打着“牙梆”…… 据说,两千年前,秦始皇派人去东瀛给他找长生不老药的时候,派的是五百童男配五百童女。他这样安排是希望他们能够男女搭配起来,生息繁衍,世世代代无怨无悔地为他找药,再也不必回来找朝廷的麻烦。事有凑巧,江梅和祥子他们这一行十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恰好也是按一模一样的比例搭配的——五个童男配五个童女。不过,他们可不是替什么人去找什么药的,他们是响应“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前天,在斯大林广场那个二十万人的“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他们这些人,都是情绪亢奋地喊了口号的。那情景,到现在都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个早晨,装得下二十几万人的斯大林广场上,人山人海,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就着苏军纪念塔,搭起了一座宏伟的主席台,主席台的上方,几十米长的巨型横幅大红标语上,刚劲有力的粗体仿宋大字,虎背熊腰地写着“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两边的两米宽的竖条,一条写着:“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另一条写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众人用长杆挑着的,手里擎着的小旗上写着的标语、口号更是多得叫你眼花缭乱。火炕一般大的圆形羊皮大鼓,一共八面,每一面都由八个人围着,在主席台前齐刷刷地一字排开。八八六十四条壮年汉子,穿着清一色的民族服装,斜露着半个膀子,肩上斜挎着披红的彩带,忘情地用大腿一般粗的胳膊挥舞着胳膊一般粗的鼓锤,敲着一个相同的鼓点,整齐划一,震耳欲聋: 咚、咚、锵, 咚、咚、锵, 咕咚咚、锵、锵, 咕咚咚、锵、锵, 咚锵咚咚锵…… 数不清的管乐方阵,依然八八六十四的阵容,两只手里举着吹的,胳膊底下夹着吹的,肩膀头上挂着吹的,脖子上面套着吹的,清一色黄灿灿的西洋铜管乐器,吹得人心里发麻,耳朵根里发痒;相对土气一点的民族乐队,更是不甘示弱,同样八八六十四的队列,横着吹的,竖着吹的,掌心里捂着吹的,两个人抬着吹的,腮帮子一律鼓成羊蛋子一般大的气球,一张一弛地把长短不齐的各色家伙吹开了花了,吹炸了肺了……二十万人,没了命地扯开了喉咙,运足了小肚子以下的丹田之气,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整整两个小时。台上的领导,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台下的孩子们,二十万人,二十万张嘴,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聊天,谁也不知道谁说了些什么。 “进行大会最后一项,”谢天谢地,终于听清了最后一句,“让我们齐声高呼口号……”这一个上午,各级领导该来的都来了。他们像打扑克的出牌一样,轮流讲话,每一个人都把上一个人刚刚讲过的话重复一遍,谁还管他们讲的是什么。这一回,终于轮到了大会最后一项。 一男一女,两个规规矩矩的知识青年代表,像马戏团里从后台放出的训练有素的猴子一样,跃然台上。他们十分乖顺地从领导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喊口号的单子,领着台下二十万人,嘹亮地呼起了口号: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 震耳欲聋,惊天动地。 口号那个东西,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明的,它能把人给喊疯了,喊癫了,喊痴了,喊狂了,喊得你脑子里一片空白,喊得你明摆着六亲不认,喊得你两眼呼呼冒血!况且,越是人多喊越好,像现在这样,二十万人歇斯底里一起喊,那声势,浩翰得叫五岳为之发抖,叫江河为之倒流。眼见得天就要撕破了,人们还在没了命地喊: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一颗红心交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发了疯的斯大林广场,一下子变成了翻滚着革命血浆的红色海洋。主席台上的巨幅标语是红的,迎风招展的大小红旗是红的,胸前别的毛主席像章是红的,手里拿的《毛主席语录》是红的,就连嘴里喊出的口号也都变成了血一样的红色。孩子们的眼睛,像抽足了鸦片一样,也都红了。一时间,斯大林广场变成了一锅烧红了的铁水,一座爆发了的火山。 天全黑了,风还在吼,雨还在下。偌大个旷野,仿佛一下子掉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深不见底的黑洞。分不出东南西北,辨不清前后左右,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这个黑得对面看不见人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暖意,不见一户人家,不存一线光亮,只剩下淋成落汤鸡的五对童男、童女,还有两个不知所措的大人和一头半死不活的牛。 未及割倒的一人多高的庄稼,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风雨夜中发了疯似地摇曳着,发出鬼哭狼嚎般的怪响。凛冽的西北风,没命似地嘶吼着,似乎要把这群吓破了胆的孩子,连同关于他们的一切,统统从这个他们还未曾认识的世界的历史上一笔抹去。李队长说,他的女儿此刻也许就行走在这个风雨夜的某条小路上,看着眼前十个魂飞胆破的孩子,他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庄严地要求大家,把各自的被褥翻出来,无论多么湿,也都要围在身上。孩子们手拉着手,身上缠着精湿的被褥,面向外,团团围坐在瘫痪的行李车上。童男童女们,要在这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等待着希望渺茫的援军的到来。李队长又重新调整了男女生的位置,他把男生和女生们间隔开来,让每一个男生拉着两个女生的手,每一个女生也同样拉着两个男生的手。他悲壮地嘱咐大家,要求每一个人今生今世记住今夜的日子,记住自己的左边和右边拉的分别是谁。无论发生多么恶劣的情况,谁都不能撒开手,死也要死在一块。 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的,黑暗的风雨中,出现了一片亮点。“前面就有人家﹗”江梅高兴得大喊起来。待众人定睛看去,却发现,那些亮点竟是淡绿色的,而且正在迅速移动。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们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那群绿色的亮点便一步步向他们逼进过来。快到近前时,它们突然疏散开来,把十个孩子、两个大人和那头半死不活的牛紧紧围在中央。那头老黄牛,突然支楞起耳朵,紧跟着一阵剧烈的骚动,它似要站起来,试了几试站不起,就又原地趴下了。它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怪响,嘴角上吐出一大堆白沫。赶车的钱大爷见状,大叫一声: “不好,狼来了﹗” “哇……”孩子们全吓得大哭起来。 “不要哭,你们大家抱成一个圈,谁都不要动﹗我来划火柴﹗狼怕火﹗” 老大爷赶紧去腰里摸火柴。天哪,哪里还有火柴?摸出来的全是烂泥一样的纸糊﹗李万昌队长一把将钱大爷拉到身后,叫他跟孩子们抱在一起,自己一步站到前面去。 “我有打火机!”可是他忘了,哪里还有什么打火机?他的打火机早就跟他的黄军装一起,垫在车轮底下,就连那件球衣也叫他不知道摔在了什么地方。要不是孙志早些时候从自己开花的行李里抽出一件衣服给他穿,他如今还光着膀子呢! “嗷……嗷……嗷……” 绿色的光点在风雨交加的黑暗中频繁地变换着位置,把十二个人和一头牛紧紧围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的圈子里,它们如何肯轻易放过这顿寒冷的风雨夜中唾手可得的丰盛晚餐? 怎么办?不光孩子们怕,钱大爷也怕,李队长自己也怕,大人、孩子,谁都是人哪! “嗷……嗷……嗷……” “早穿棉,午穿沙,围起火炉吃西瓜。”这是辽北十月天气的生动写照。赶了两天路的孩子们,风雨中步行近三十里,如今又受困在这个寒夜中风雨交加的荒郊野外。此刻,在一群饿狼的层层包围下,他们正在默默等待着死亡的来临。饥饿、寒冷、恐惧和绝望一下子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斯大林广场“抽”的那点儿鸦片早就过了劲。童男童女们终于一下子清醒了,长这么大,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他们突然发现,在这个风雨交加、饥寒交迫,又被饿狼围困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荒郊野外,什么革命,什么再教育,什么反修防修,一切都是谎言,只有生存才是最实际的。没有谁能够救他们,能救他们的,就只有他们自己﹗求生的本能叫他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生命,生存的欲望叫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男孩子们首先振作起来,振作得像五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此刻都正拉着两个女人的手。他们死了不要紧,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女人的生命需要男人的保护;女孩子们也开始安稳了,她们知道她们就要死了,可是,她们还知道,在她们死的时候,她们每一个人的手,都由两个男人紧紧拉着,这个世界上,还有最后两个可以信赖的男人和她们死在一起。 江梅的左手被孙志的右手紧紧地拉着,她的右边,就是跟她一起长大的祥子哥。此刻,江梅似乎也什么都不怕了。 “祥哥,和你死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后悔,真的!”江梅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对祥子说这样的话。她不怕羞了,她知道,他们就要死了,她再也不怕别人笑话了,临死之前,她要给她的祥子哥留下一句她最想说的话。 “不要瞎说,还没到最后时刻﹗”祥子大声喊着,伙伴们全都听得见。他死死拉住江梅的手,把牙齿咬得“咯嘣嘣”响,他要把死亡来临前的那份恐惧一个人承担下来。 “祥子哥……” “想起来了,我身上有刀。”祥子突然想起,他身上竟然还有一把刀!那是一把老式的木把折叠水果刀,是他妈叫他带的。他嫌样子丑,不愿带。他妈说,“木头把怕什么,总比没有强。带在身上吧,反正也不沉。乡下有的是苹果,吃的时候打打皮,省得有农药,不卫生。”他从裤兜里摸出那把妈硬要他带上的折叠苹果刀,心里顿时升起一阵悲凉。“妈……”他在心里轻喊着,把折叠刀展开,紧紧攥在手里,叫右边那个女生抓住他攥刀的右手腕。 “对,祥子说得对,我们人多,而且身上还有刀,它们不敢!”孙志也坚强得像个大人。面对着五个朝夕相处的女同学,他还能做什么?也许下一秒钟就是最后时刻,是到了拿出点男人气的时候了。 “要是有个手电筒就好了……唉呀!手电筒……我带来了!我想起来了,可能就在你的行李里!”江梅突然冲祥子大声喊起来。她记起来了,前天早晨送行的时候,她爸爸给过她一支五节电池的军用手电筒,说带着它,乡下也许用得上。她不想要,说行李卷塞不进去。当时,她爸爸似乎说要把手电筒塞进祥子的行李中了。当时人多,闹哄哄的,不知道塞进祥子的行李里没有。“爸爸,你塞进去了,是吗,一定是的,爸爸,你可真伟大!”她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在心里祈祷着,呼喊着她军人的爸爸。 多么伟大的父亲,多么了不起的发现﹗祥子撒手翻身到车上的行李中,一口气摸出了自己的那个早就散了花的行李卷,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倒出来,抖落得遍地都是,终于,那个宝贵的手电筒摸到了﹗ 这个重大发现不亚于给每一个人带来了一线生命的曙光。李队长一把将手电筒抓在手上,一道雪亮的光束,顿时穿过雨丝,在黑暗中凿出一个光明的洞。他把光束射向围着他们的狼群,天哪﹗果然有二三十只,每一只差不多都有牛犊子那么大! “嗷……嗷……嗷……嗷……” 狼群见了突如其来的光,四散开去,叫得越发吓人了。手电筒的光束照过去,它们便迅速闪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又换一个角度,重新围将上来,而且,包围圈比前一次更小,它们太饥饿了。李队长只好按顺时针方向,首尾兼顾地一圈一圈照下去。他哆嗦着,双手抓着手电筒,越转越快。然而,狼们终于领略到,他们除了一只会转圈的手电筒,大概再没有什么更新的威胁,于是,当它们最后一次围将上来的时候,包围圈小得叫他们闻到了狼身上那湿淋淋的毛腥味。 狼群在一步一步逼近,包围圈在一寸一寸缩小,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孩子们手拉着手紧紧聚在一起,不悲、不伤、不呼喊、不哭泣,只是彼此挨得更紧了。祥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后一次抓紧江梅的手。他把右手上的刀拿下来,含住刀背,把刀横着叼在嘴上,腾出手来重新抓紧右边的女生。江梅最后一次把身体紧紧靠过来,她死死偎着她的祥子哥。不重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能跟她的祥子死在一起,什么就都不重要了。 钱大爷李队长的真魂也都吓飞了。他们恨自己生不出三头六臂,他们恨自己保护不了十个孩子。他们最后一次尽可能地张开双臂,恨不能把十个孩子统统搂在怀中。十二个人,十二条命,就这样紧紧地抱成了一团,闭上眼睛迎接着那个最后的一刻。 突然,李队长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背毛主席语录?!于是,他用平生最大的嗓门,背出了那条曾经帮他历经千难万险的一条: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童男童女们,撕破了嗓子跟上来喊。 “排除——万——啊!”赶车的钱老大爷刚刚喊出半句,一只最先冲上来的野狼把他的裤子撕去了一条儿。 “啊……啊……啊!”十二个人,十二条命,十二个生灵,十二个强烈的生物本能,叫他们用平生最大的气力,喊出了十二个最歇斯底里的求生欲望。 “突……突……突……”远处似乎有拖拉机的声响,那声响越来越大,两道雪亮的光柱随即平射过来,已经扑到身上的狼群“嗷、嗷”怪叫着一哄而散。一个嘶哑的声音狂喊着: “喂……你们是来葱屯插队的知——青——吗?” “妈……呀﹗” “妈……呀﹗” 十个哆嗦成一团的落汤鸡,十个对生命已经不存希望的童男童女,十个阴曹地府门前掉回头来的苦难生灵,一把撒开早就冻僵在一起的手,仰面朝天躺倒在漆黑的泥水里,咧大了嘴巴,两天来,第一回对着深不见底的天,放开了哭声…… (2003-07-23) (责任编辑:冒冒) |
| 投稿 评论 上一页 下一页 回顶端 |
| 华 夏 知 青 网 版 权 所 有,未 经 作 者 允 许 禁 止 转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