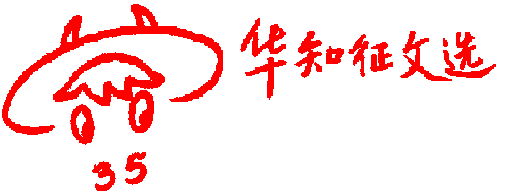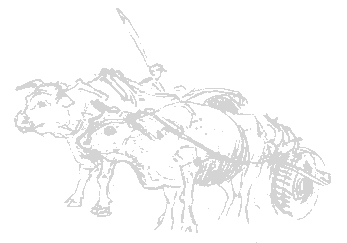游荡一生,偶然游经此地,见一些同时代同经历的GGJJ在此张贴煽情,引我忆起些许陈年旧事。
我像早年革命者,不论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宪兵营、特务队,打死也倒不出革命情报。碰上组织,不知怎么一抖擞,居然从衣夹缝里抖出组织关系来。我不是写手,更不是间什么杂品仓库,深知游者忌负重行道理,清理过无数次的破夹袄,如今怎么就抖擞出这陈谷子烂芝麻?
保不准被GG、JJ提溜一抖,还能抖出些旧东东。既然夹袄有遗留物,索性抖给组织算了。
一、下乡记
那年我刚16岁,不谙世事一少年。
着实享受一番国内免费游(大串联)后,紧接一阵造反、夺权、武斗、无政府混乱,学生成了政治家的马仔,本不懂政治的我忒烦。父母双双住在学习班(牛棚),家里几个孩子无人看管,早先那点自由快感没了。
忽一日驻校工宣队通知返校“复课闹革命”,到校看看也就学学最高指示,没劲。不久传达“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最新指示。1969年初,学校贴出上山下乡报名启事,撩拨我荡心劣根死灰复燃。少不更事,压根不懂“扎根农村”前俩字,只觉得另一次免费自助游来矣。瞒着家人报了名,张榜时被同校二姐发现。二姐对我铁了心要去无奈,转而劝我挂靠就读另校的三姐搭伴落户。寻思,同为三峡纵深,不过江南江北之分,无碍,便欣然应允,于是那年我成了“知识青年”。知识乃刚算术换了代数,初中一年;青年乃尚未脱离监护期,稚气未脱。好在0.6+0.6也算有位整数,未经评定就晋了“知青”职称。
1969年 3月18日天没亮(一生事件无数,就这日子记得清),我背上行李去三姐学校,黑暗中新同学面孔还没辨清,稀里糊涂就被装运到长江边,河滩上数万人头攒动。沿公安严守的摇晃跳板,踏上隐约泊在江中的轮船。送行的人被强行推回岸上,震耳欲聋的嚎啕和声嘶力竭的临行嘱咐,还是越过公安的防线从身后传来。回头望望黎明中守候的人群,还真有点敦克尔刻撤退的阵势,不过更像燕太子丹送荆轲出征场面。我没家人前来(父母学习班不准假),也没同学送行(我们不同行程),倒少了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受。
船上广播,全体船员上甲板劝阻堆积船舷的知青,以免倾覆。我没人可告别,趁机钻进厨房捞走一包半生不熟的肥肉。
天明,船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缓缓驶离。霎时岸上船上哭声一片,地动山摇。视野中慢慢缩小的重庆,渐去的哀嚎,这艘绑着两只驳船的“长二捆”,顺江而下开往万县。同船几千知青登录底舱平台,蒙头就进入17世纪欧洲人往美洲贩黑奴的镜像站点。从此都感染上一种新型病毒,长出一个结瘤,学名——知青情结。
两天漂泊到万县,河边等着数百辆解放卡车。晨曦中,一车车黄军装浩浩荡荡经过城区,俯视沿街欢迎的人群,犹如巴顿的远征军或戴高乐的自由法兰西军团开进战后的巴黎。长结瘤的知青肾上腺素猛增,没了两天来生离死别的忧闷,没谁领头,齐声唱起《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引来满街口号、掌声,歌便唱得更欢,语录歌、苏联歌、样板戏此起彼伏。
出得城来,车沿山路蹒跚爬行,荒凉苍劲,歌渐稀疏,慢慢发现同行车少了许多。及至中午见群山环抱一大块平川,觉着不错。同行公社干部介绍,当地有“金开(县)银万(县)”之说,思忖旅游到此为止,不想车竟穿城而过,一头又扎进山里,同行车更少了。当我发现山路上只剩这辆车时,已是下午时分,最后停在一个叫高升的地方。
几十人跳下车来伸伸麻木的腿,就见一群拿扁担的乡民候在路边,等七手八脚卸下行李,公社干部才说还有三十里山路要走。一听这话,早已沉重的心情又多几分分量。一路磨蹭,到得山顶幺店子(有一古树,两三间草屋;贩夫走卒可沽酒就干蚕豆的小店。类似武松打虎前先喝三碗酒的那地儿),队伍已拉了足有一里路长。俯身望着一路哭泣而上的女生,空有英雄救美之心,憾无拈花扶草之劲。看天色不早,挑夫早走得没了踪影,还有十五里下山路。公社干部猴儿急,催赶我们穿箭竹林,跨溪涧。沿途风景极美,绝不亚于九寨沟,可惜那时我们精贵的是腿,眼球可没法顾及。
天早黑尽,见黑雾笼罩,两山握持,涓涓溪流处袅袅炊烟,终于到达麻柳公社。欢迎仪式极简,山民善歌寡言,省了寒暄,每人一碗肥腊肉就米饭(以后我才懂那小碗肉之珍贵,乡民款待之隆重),饭后谷草堆里倒头呼呼入睡。天亮方见小镇全貌,二三十米石板路,两排木屋背山面溪,人口不足五十,故事还不少——此乃后话。
早饭后宣布分队,各自记下生产队番号,依依惜别认识几天的同学,跟了挑夫,向四面八方山里散去。
我与姐随挑夫上路,年轻人易熟,几句聊开才知他是小队副队长。十五里上山路边聊边看,倒少了一些劳累。知这群山重重叠叠延绵川陕,人烟稀少交通闭塞,难怪当年红四方面军要在山里闹革命,我要是国民党也不到这儿来追他们,让他们在山里穷折腾。
中午时分,远远见大山胸腹被扒开一大片空白,肋骨样梯田层层排列在大山裸露的胸口,右乳部一小块平坝站满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那群人是我迄今见过最纯朴的,从他们张开后合不拢的嘴,从沿着嘴角悬挂的清涕,从直直粘到我身上的眼球……你能感觉他们内心冒出若干个“?”和“!”。我及我的户口被这些人簇拥着,落户进旁边惟一突出、乳头般孤零零的茅屋——生产队保管室。在这里我开始与他们共同打理这块裸露的胸脯,以后还剃过山头,修过山脚,接受着他们的再教育。
(2003-12-03 于 )
(责任编辑:冒冒)
|